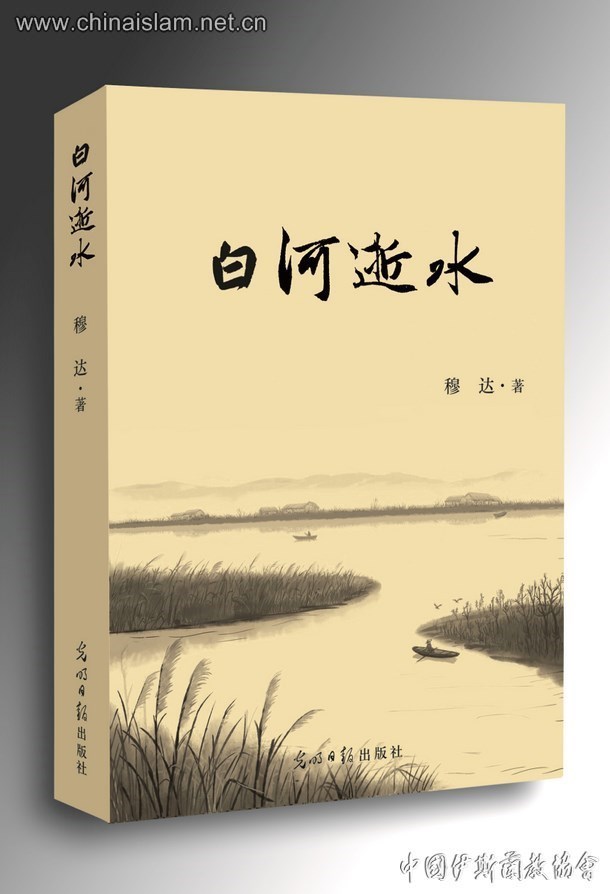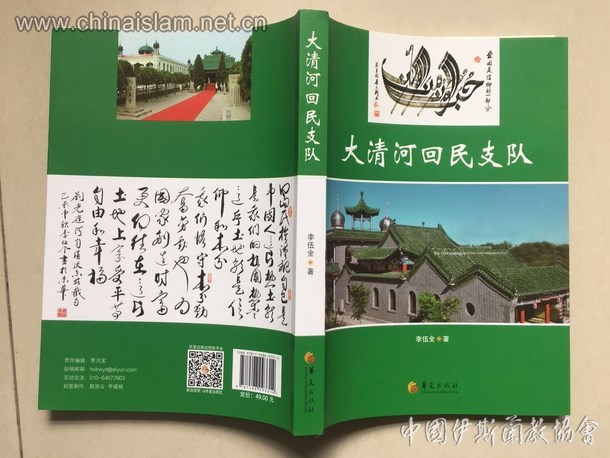试析《白河逝水》结构的审美意义
穆达先生是南京回族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白河逝水》完稿后,曾两次请我审读小说中所涉民族宗教内容,于是我有机会成了这部小说最早的读者。当我读完小说时,内心有一种隐隐的震撼。这种震撼不止于小说真实典型地再现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也不止于对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回族穆斯林生活的生动描述,还在于小说的结构形式以及这种结构的审美意义。
这部小说以韩伯之和二秃父子不同的人生命运为主线,描述了中国底层民众在复杂动荡的社会变迁中的生存状态。小说的时代背景跨越大半个世纪,有故事的人物林林总总不下二三十人。作者别具手法,以两条平行的线索展开叙述:一边由“我”描述当下人事,一边由“外公”讲述当下之前的故事。由于历史的内在联系性,这两条线索错综交织,融合渗透,互为观照。外公五个独立的故事像断代史一样连缀起来,自行成篇,又被有机嵌入“我”所描述的当下时事中,使全书内容浑然一体,最终展现了一幅宏大的中国乡村社会动荡变迁的历史画卷。这种不同于通常的线性结构方式,就我所知,在以往长篇小说中很少见到。
小说通过讲述历史塑造了一个典型人物——韩伯之。韩伯之不仅是传统乡绅的代表,也是一个文化符号。历史上中国乡村的治理往往是由乡绅阶层来完成的。他们依靠自己的文化教养、伦理观念和个人威望主导乡村建设和管理。尤其像韩伯之这样在民国之后接受新思想的乡绅,在动荡时代表现出鲜明的道义担当和人文情怀。而后来这个阶层的凋零消亡,也就代表了传统乡村治理的解构。小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韩伯之和一位回族女子的私生子二秃,主要通过“我”来描述。作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渔民,二秃屡受侮辱与损害,他把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视为不幸命运的一次咸鱼大翻身的机会,其作为和遭遇既可憎又可怜。两位主人公虽生活于不同时代,其命运不同,但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某种程度上的错叠和复制。这是作品的一项重要表达。小说并没有进行正面描述,而是把它隐含于平行交错的线状复式结构中,通过这种结构所产生的相互观照和比对,不动声色地完成了二者之间的勾连与过渡。
这种结构形式不仅使冗长的时代和繁纷的故事得到轻松有致的安排,以时代和人物交织叠印深化作品思想内涵,而且使故事有如绘画之留白给人以不尽的想象。例如武昌起义后集体加入革命军的西龙山土匪光复南京前到白河镇抢劫,半个世纪后同样从西龙山上下来的“工总”队伍为消灭“联总”到白河镇打砸抢;抗战期间国民革命军的勤务兵赶猪从教门聚居地经过被愤怒的穆斯林捆绑起来逼得营长自打耳光赔罪道歉,十年浩劫时堵在达玉兰出殡途中的骄狂的红卫兵队伍在伊玛目“真主至大”的高声诵念中被斥退;还有白河镇民众犒劳胜利者的情景在不同时代重演、清末民初的笃志小学堂校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奏响……等等,这种复式结构所生成的审美效果,还在于这种大构架下对文字、节奏、色调等元素的精致处理和一些技法的综合运用。小说在线性展开的缝隙里,不断通过倒叙插叙补叙,使故事的演绎跌宕起伏,摇曳生姿。如小说第四章,在描写风雨如晦的时势和阴霾生活的同时,突然宕开一笔,以舒缓的节奏插叙了主人公二秃在白河水边邂逅爱情的一段,用色彩斑斓的文字和歌谣描绘了夕阳水边的一对男女质朴的情爱,使小说的基调陡增一丝暖色。而在接下来的倒叙中,作者用较快节奏叙述了达玉兰被西龙山土匪乔装挑夫绑票,而后哈少坤赎人、韩伯之救人的故事。这段故事情节完整,波澜叠生,富于传奇色彩。尤其是最后韩伯之仗义孤身虎穴救人,二人纵马河岸的画面,使小说在风云惨淡的底色上平添了浪漫色彩。这种在情节节奏上的张弛相济,画面安排上的冷暖相调,大大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让这两条线索(两个不同的时空场景)交错构架是不容易的,它不仅需要二者在表现形式上严丝合缝,更需要其内在思想脉络的有机联系。小说主要通过情节的照应来完成这种联系。例如通过对地痞大胡子(花五子)的反复描述,包括大胡子获取土匪没有得到的一对玉爵等,使这个痞气十足的人物的行为一以贯之,深刻揭示了中国底层社会政治生态的吊诡——和许多底层人物坎坷不幸的命运相比,大胡子却能在不同时势中一直得势,甚至连韩伯之也始终没有逃脱他的魔障。这种情节的流连照应,使故事的内在联系十分紧密。
《白河逝水》整体结构展现的审美效果,还得力于作者的语言功力。小说的语言明快生动而富于张力,又多用俗语、歌谣乃至词赋,表现形式丰富,独具语言风格。小说中既有如尖刀般突然切入历史和人物心灵深处的文字,让人一颤;又有不少象征和隐喻,如旧驿铺最后半截拴马石对时事的见证,一直作为主要人物命运象征的那株老槐树被雷电劈倒;又如“王家门口陡然刮过一阵阴风,风卷着黑蝴蝶一样的树叶子嗖嗖怪叫,满树盛开的槐花一夜间被吹落得干干净净”……这类风咽鹤泣的诡异场景对人物命运的隐喻等等,读来都令人震撼。
长篇小说是一种结构性很强的文学样式,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它的思想性。《白河逝水》的结构当然是为思想和主题服务的。进入小说尾声,在历经风云激荡的岁月之后,中国乡村渐趋于平静和正常,那些蕴藏于民族血脉里的人文精神和人性之光并没有完全泯灭,遗落在民间和底层的亲情、爱情和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也渐渐复萌。特别是历经劫难的主人公二秃回归“伊玛尼”的省悟和寻求灵魂的自我救赎,这样的结局,读来同样有一种动人的审美力量。
这不是大团圆的结局或结构,而是两条平行线索交织共进的结果。故事结束在改革开放到来的崭新时代。这是作者的一个良好愿景,因为这个时代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构着中国乡村的社会形态。